你未来的钱会去哪儿?

美元病了,病得还不轻。
这是一种无从预防、无法治愈的经济绝症。
美元就像一棵大树,虽然看起来仍是枝繁叶茂,但肌体早已被一种隐秘而致命的病菌所侵蚀。这种病菌十分古老,从人类第一次交易开始,它就存在于经济规律之中,并伺机发作,置人于死地。
美元并非第一个受害者。在这之前,它折磨过几乎所有的经济霸主,如同一个最恶毒的诅咒。可惜人类从来不长记性,不断重复着过去的故事,所以永远摆脱不了它的纠缠。
这个病毒到底是什么模样?为何人类最聪明的头脑们都无法研发出一劳永逸的疫苗?我们又该怎样觉察迹象,及时抽身,减少自己在这场金融疫病中的损失?
也许,咱们可以忽略掉艰涩的理论知识,从一件极小极小的小事讲起。
资本主义杀死了资本主义?
1913年,有一对原本生活在曼彻斯特的夫妇,决心搬到伦敦去居住。不过,为了搬这个家,他们需要舍弃家里全部的电气设备。
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英国,有70种不同的发电站、50种供电系统、24种电压和10种频率,工业标准十分混乱。这确实很不方便,但也没有办法,小工业主所有制是大英帝国工业版图的基础,是英国这棵大树的“根”。
在很久以前,这副根系就已经感染了一种叫作“食利主义”或“资本主义”病菌,渐渐地无法再为树木提供营养。
听到这里也许你会奇怪,资本主义杀死英国?资本主义还将杀死美国?资本主义杀死了资本主义?这是一个什么鬼打墙的命题?
让我们继续讲完珍妮一家的故事。
这对夫妇原本在曼彻斯特开了一家工厂,赚了很多钱,成为了一夜暴富的“新贵”。看过《泰坦尼克号》的人都知道,“新贵”最迫切的心愿,都是想法设法打入“老钱”的社交圈。搬家去伦敦是必须的,送孩子读贵族学校也是必须的。不过在搬到伦敦那天,珍妮的大儿子蹲在插座旁边突发奇想:“妈妈,为什么不能和女王建议,让整个英联邦都使用同一种电气标准?”
他得到了一番严厉的批评:“亚历山大,你即将去读伊顿公学,不要开口闭口都是钱,也不要提到家里曾经开过工厂。我们再也不用干那种脏累活儿了,你父亲在海外的投资回报,已经足够让我们过上贵族生活。”
当珍妮决意关闭工厂,成为一个食利者,并期待自己的孩子成为下一代食利者,英国与美国的霸权之争,便注定将以失败告终,毕竟国家实力才是国家竞争的唯一底气。
谁制造,谁产出,谁制定工业标准,谁才握有现实世界的最终话语。
不过在1913年,英吉利这个巨人,并没有看到发生在脚下的危机。也许它关注到了一些数字上的变化:比如,大洋彼岸有个叫美利坚的暴发户,工业生产力已经是自家的两倍,甚至隔壁有个叫德意志的乡下人,都开始超过了自己。但这有什么关系?英吉利手握着英镑,英格兰银行是整个英联邦的央行,光是靠宗主国地位,通过资本增殖和国际金融服务,就能让帝国继续辉煌。
这场天朝上国的美梦清醒在1944年,一个名叫布雷顿森林的地方。
尽管英国派出了凯恩斯作为谈判代表,但还是无力挽回英镑霸权瓦解的必然结局。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被迫签字,同意将英镑霸权让渡给美元,从此美元成为与黄金挂钩的唯一货币,并获得了一系列的特权:比如国际铸币税,花3美分的成本印一张绿纸,可以跟其他国家买100美元的东西。比如跨国经营网络,美国的公司、银行、保险、会计师事务所、评级机构所构成的利益一致性主体,比维多利亚时代遍及殖民地的英国商船,更容易攫取利益。比如货币操纵,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发生,美国通过金融市场操作,兵不血刃就能迫使英法改变军事行动。比如打击竞争对手,20世纪80年代,纽约广场饭店一纸协议,便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打得一蹶不振。
英国何尝不知,它所让渡的权力至高无上,但凡可以选择,它不会同意签字。然而,英镑之树早已失去了根基。缺乏国家实力的支撑,由虚拟货币撑起的霸权注定是不能长久的空中楼阁。
美国制定全球秩序,开启全球化狂飙的黄金20年
二战爆发后,英国急于得到美国的支持。昔日霸主像一支被不断挤压的牙膏,被迫一点点地吐出了大英帝国压箱底的资产——从黄金储备到军事基地,以换取美国提供援助。
只有凯恩斯等人还在苦心孤诣地设计战后秩序,想在战后为英国争取与美国“共同的特殊地位”。而美国人则在利用“租借法案”不断地逼迫英国做出让步,以消灭那个有可能在战后格局中成为美国对手的大英帝国。
罗斯福不是威尔逊,他不会让美国在世界牌局上再出现一战之后的冒叫。在大战刚刚打响之时,罗斯福就组织起跨政府部门的重建委员会,与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外交政策委员会等智库,开始设计完全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欧洲战争爆发二周后,国务卿赫尔在国务院建立了“和平与重建问题委员会”。美国财政部、副总统华莱士也组建了类似班子。
在美国设计的秩序中,包括组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国际联盟和安全理事会等组织,也包括确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金汇兑制。
二战后的美国已大棒在手,因此没有必要再采取一战后的逼债战略,而是改弦更张,推出了无偿援助战后重建的“马歇尔计划”。美国人心里清楚,既然战争已经彻底摧毁了由欧洲主导的世界秩序,那么它要做的就是在废墟上重建美国秩序的大厦。
通过“马歇尔计划”,美国扫平了欧洲国家屹立了数百年的市场城堡,把除苏联控制区以外的欧洲都纳入美国主导的大西洋经济圈。到1951年,所有欧洲共同市场国家(OEEC)的工业产量都超过了战争时期的最高值。而它们之间所进行的国际贸易,都必须依赖于美元——这是美元主导下的复兴。即使是苏联主导的经互会组织,若要与世界经济体的其他部分进行贸易或投资活动,也离不开美元。美元替代黄金成为控制全球交换的权杖。
为了除掉欧洲列强在世界各地残存的殖民地壁垒,美国通过推进“全球非殖民化”运动,最终形成了以美国为核心的一体化大市场。“马歇尔计划”促进了欧洲共同市场的发展,创造了能够消化美国剩余产能的欧洲市场,并为美国资本的全球扩张扫除了国际政治和经济的障碍。从此,美国可以通过美元体系对全球经济进行符合美国利益的整合,而国际政治也被笼罩在美元体系的影响力之下,开启了美式全球化狂飙突进的第一个黄金20年。
美国的货币,世界的问题
二战结束之前,44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国家公园签署了有关文件,从法律上确认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诞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意味着世界金融市场美元化的开始,是美国登上世界权力巅峰的标志。
从设立之初起,美国就试图把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这就决定了这一全球货币体系的命运——被美国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因此,从经济与货币的角度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尽管存在着凯恩斯、特里芬等人所揭示的缺陷和悖论,但只要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就要让它运行下去。
布雷顿森林体系具有“金融抑制”的特点,它不允许私人金融机构在国与国之间自由移动资金,只允许私人为贸易和生产性投资为目的移动资金,国家有权对金融和资金流动予以干预和管理。因而,以迈克尔·博多的国际货币体系九大指标来衡量,布雷顿森林体系在通胀率、人均收入增速、货币供应量、短期和长期名义利率、短期和长期真实利率、名义和真实汇率的绝对变动率等各方面都是所有国际货币体系中最稳定和经济表现最佳的体系。尽管如此,它仍是一个短命的体系。它的迅速瓦解与它的横空出世一样,不在于其经济和货币方面是否存在着悖论,而在于它对美国利益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当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长康纳利对全世界银行家说出,“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的时候,不仅是在表述一个国际货币的问题,也是在挑明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关系——谁服从谁的问题。
在国际政治的视角下,布雷顿森林体系蕴含着一个深刻的国际政治学难题:世界货币体系在霸权国家利益至上的框架下,如何才能维持全球性体系稳定运行的目标?
囿于专业训练的局限,大多经济学家擅长用经济学的框架分析货币,却没有看到或有意忽略了货币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影响,也难以看到世界货币体系的国际政治意涵。当货币还是一国货币的时候,货币体系的影响通常局限在国内,一旦成为世界性的货币体系,它就会对国际政治经济乃至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是支配性的作用。对这一点,政治家虽然没有深刻认识,却会根据国家利益、按照政治直觉做出选择。罗斯福选择了金汇兑制美元的生,尼克松却决定了它的死。布雷顿森林体系生与死的关键,都是战争——它生于二战,死于越战。
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着眼点,是为了二战之后的经济恢复,其中特别注意汲取了一战之后世界金融危机转向国际政治危机的教训——就是要防止恶性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导致的社会动荡。可以说,这是一个基于建设目标、具有权力制衡设计的世界货币体系。然而,二战之后不久,美国在亚洲陷入了两场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战争需要大量的融资,美苏冷战的“和平竞赛”也需要大量的资金,约翰逊“大炮加黄油”的政策更是极大地增加了财政赤字。为恢复战后经济,具有建设性目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尤其是金汇兑制,难以满足为战争融资的需求。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金汇兑制的真正死因。没有什么体系是完美无缺的理想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的生存与延续不在于它有没有缺点,而在于它是否能够适应变化去满足需求——在体系主导者与从属者的利益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
在美欧日之间几番博弈后,美国政府导演了人类经济史上最为大胆的赌局。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国停止承担对外兑换黄金的义务。此后,外国人持有的610亿美元的债权只能以其他债务凭证的形式进行清偿。这实际上是单方面宣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尼克松之所以敢于如此下注,除了靠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支撑之外,还有美国经济学者对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后果的深入研究。在美国人看来,大量国际收支赤字的存在有利于美国。
作为过于政治化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它的生与死,主要是基于美国的国内利益和国际战略的考量,而不是出于全球经济体系的金融稳定、经济互助和国际合作的需要。美国利益最大化,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徒然具有全球货币体系之名却难以承担起全球货币责任的根源,也是它在世界舞台上来去匆匆的主要原因。
美元本位制赋予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几乎可以任意印制美元和发行美国国债的权力,却不必承担保证美元币值稳定以维护世界金融体系稳定运行的责任。基于这种权力与责任不对等的美元本位货币体系,衍生出了不平等的美元币缘秩序。美国通过对全球货币体系的控制权,拥有了美国资本和美国利益凌驾世界其他国家利益之上的特权。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这种基于货币特权之上的“美国帝权”,是与大英帝国“自由贸易权”类似的“非领土的权力”。这一权力的核心就是货币与资本的霸权,即通过对货币发行和金融市场的控制不断获取超额利润的权力——币权。货币—资本霸权是综合性霸权,它不仅体现了经济的力量,而且是一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乃至军事等多种力量协调配合的果实。
产业空心化,流金岁月后的寒冬
在虚拟资本主义体制下,实业成为金融资本增殖的累赘。随着金融化的普及,美国出现了产业转移的浪潮。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产业开始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移。美国制造业的转移,主要通过对外投资来实现。1977—1982年,美国在发展中国家每年投资增长率为13.3%,在其他发达国家则为82%。到80年代,美国制造企业几乎停止在美国国内生产,主要通过购买制成品贴牌后进行贸易。据保守估计,到2001年,美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FDI)达到3580亿美元。在海外投资浪潮中,金融投资增长势头更加迅猛。1964年,美国主要银行的海外资产为70亿美元,而到1974年,美国银行海外资产达到900亿美元,利润额占总利润的30%。
20世纪70年代,资本的全球扩张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出现了以产业大转移为特征的全球化浪潮,催生了一批被称为“小龙”、“小虎”的新兴国家和地区,连中国、印度这样长期在经济上自成一体的大国也从80年代开始先后实施改革开放,积极吸引外资,积极向国外出口逐步融入了全球产业链。这些新兴国家和地区快速发展的秘诀都是靠出口拉动,这一方面要依赖向美国市场出售产品,另一方面也要依赖美国金融市场吸收其贸易盈余以免引发本币的大幅升值;与之相对应,美国一方面要依赖新兴市场国家生产的廉价商品,另一方面也要依赖这些国家的资本净输出流入购买美国国债,以冲抵美国贸易和财政的双赤字,维持美元体系的总体平衡。据2009年的统计,美国资本净流入占世界的41.7%,而中国的资本净输出为23.4%,占到世界的近1/4。这种多个国家和经济体缠绕于美元体系的多重依赖关系,构成了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复杂关系。
经济金融化并不是美国周期独有的现象,英国周期在100年前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英国资本对来自制造业的竞争,与美国资本采取的方式一样,就是实施金融化。这开启了爱德华时代的“流金岁月”。“拥有资本的人永远能够分享其他国家脑力和体力活动的成果”,100年后的美国与英国一样,也在利用金融化的方式分享其他国家的脑力和体力活动的成果。
产业空心化,是经济金融化的副产品。对于身处越战泥淖和与苏东集团冷战的美国来说,金融化带来的收益实在是雪中送炭。更重要的是,美国从此可以用“美元货币—资本体系”来获取收益,就像用“芝麻开门”的密语就能打开财富大门,而不必像苏联那样,必须以出口石油或其他资源和产品才能获得有限的“硬通货”。放弃金本位这一原本是被逼无奈的举措,却收到了“破坏性创造”的效果,也在不经意间奠定了美国赢得冷战的最终结局。这或许是美国金融之秋的诸多收获中,分量最重的果实。
只是秋天后面是冬天,顶点过后,就是下坡。
这是资本主义挥之不去的梦魇诅咒,从实业之夏,到金融之冬,如同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总会从一个时点开始,当霸权国家决定放弃生产、坐享其成,就给自己埋下了衰落的种子,类似的故事不断重演。
如今,终于轮到了美国。
这个曾经以制造业立国,以生产力为剑,将英国赶下王座的权力所有者,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同一个恶性循环。而这一次,恶性程度更高,恶化速度更快,因为它还感染了一种新型菌株,将资本的贪婪发挥到了极致,并依靠美元的力量打破了国家间边界,将美元病散布到了全球各地。
这个新菌株的名字,叫做“赌场资本主义”。
如果将资本主义比作一个大赌场,过往的几个庄家,都还在按照传统的玩法攫取收益。金库里有多少黄金就发放多少筹码,摊子不能铺得太大,万一大家都拿着筹码来兑钱,兑不出来赌场就要关门倒闭。
但美国这个庄家,心特别得大,从一开始产业就遍布全球,东边和越南打仗,西边往欧洲撒钱,自家还过得纸醉金迷。很快它就发现,金库里的黄金已经不够用了,再这样下去,一旦发生挤兑,赌场声誉要出问题。好在赌场里有一个名叫尼克松的荷官,提出了一个天才的想法,为什么非要兑换黄金?从明天起我们直接贴一张告示:黄金不兑了,但筹码大家可以拿出赌场去用,本店童叟无欺,家大业大,绝对不会倒闭,这些筹码在外面可以永久流通,何必兑来兑去那么麻烦呢?
从此,资本这头怪兽,便从笼中一跃而出。美国此前还在村里种地、村外办厂,如今一看,只需靠着办赌场就能庄家通吃,渐渐关了厂,荒了地。而这种坐享其成赚快钱的思维一旦形成,便很难再回到曾经的勤勉踏实。族中有个名为“哈佛”的著名学堂,从前培养的学生会去往各行各业,如今大部分都选择去赌场工作,实在因为工资要比其他地方高得多。
名为美元的筹码,和食利主义的赌徒思维,逐渐往世界各地流淌。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种种怪现状,飙升的房价,剧烈的金融危机,频繁的贸易争端……其实都是美元病的表征。
体系性的崩溃难以避免:手中握着筹码的人,发现它的购买力在下降。发现赌场自己债台高筑,欠账越来越多,根本没有还清钱的一天。发现隔壁有新开的赌场,看起来更加可靠。还有新开的工厂,工作环境看起来不错,赚的也挺多……
总有一天,手里拿着筹码的人,将会回过闷来,决定给自己找个出路。那家赌场也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整天喊着“再工业化”“让赌场重新伟大”,“削减债务”,但从事实数据来看,全都是空话。
资本主义的诅咒难以逃脱,它曾经怎样杀死英镑,就会怎样杀死美元。
让我们拭目以待那一天。
如果你想烧烧脑,学术地、历史地、体系化地看一看这家赌场的未来,看看你手里的筹码会不会成为一堆废品,欢迎读一读这两本书《美元病——悬崖边缘的美元本位制》《币缘论:货币政治的演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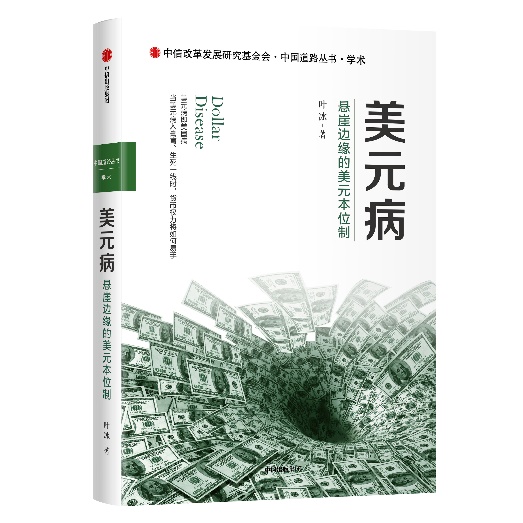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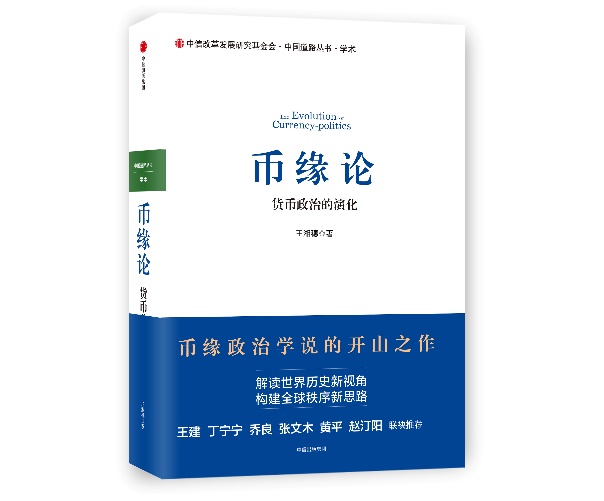
-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欧洲中欧班列网络
- 书评|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
- 除了硬核“老干妈”,世界超级富豪还有哪些乘风破浪的姐姐?
- 田文林 | “颜色革命”不是捕风捉影——读《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有感
- “技术控”海信:走进“无人区”
- 《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精彩书摘: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
- 你未来的钱会去哪儿?
- 美元是否趋向于下一个奇点时刻?
- 俄国防部:乌军一昼夜损失约1210名军人
- 宁夏银川:冰浮项目解锁冬日乐趣
- 第十五届鸟巢欢乐冰雪季正式开放 双奥地标再燃冬日激情
- 全国秋粮收购已超2亿吨
- 冰湖腾鱼!黑龙江“冷水鱼·冬捕季”启幕
- 中国驻墨西哥使馆对美方抹黑中国出口商品言论表示强烈不满
- 越南老街省发生公交车翻车事故 已致9死8伤
-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
-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0120170006
-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8263号
-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2503号
- 京网文[2011]0283-097号
- 京ICP备13028878号-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