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日报网6月4日电 IC产业是一个分工非常精密的产业,在产业的每一个环节得面临着众多的机会和挑战。相应的,唯有在很多核心环节上掌握关键的技术,我们才能在国际上掌握一定的话语权。但国内芯片设计与制造产业的真正问题在哪?这恐怕是首先最应该回答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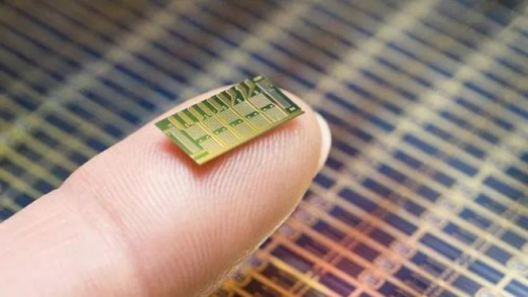
这次,由 DeepTech深科技主办的 2018 半导体产业大势论坛中,多位产业领导人物与我们分享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潜力及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可能的解法,尤其在人才的确保与产业发展方向上,各产业龙头也都发表了精辟的看法:
芯原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戴伟民表示,中国每年毕业生不少,他到电子科大每年招收硕士以上的学历同学的时候,宣讲时通常有 600 人出席,笔试以后到第二天可参加口试的还有 100 多人,所以人才还是不少。

芯原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戴伟民
但问题是刚才也提到了,人才没有办法安心在一个地方练好技能,毕竟人才的流动会造成经验无法积累,技术无法传承。
中国人才的流动性过高是一个问题,有的人做芯片是每两年换工作,这些人可能从来没有看到芯片上机测试的表现,无法印证自己的技术想法能不能行得通,虽然做了很多芯片,但实际上可能和新手差不多。因此,每两年换一个地方可能就会对人才本身的技术养成与公司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还有一个情况是并购,并购对企业的成长还是相当重要,现在中国大概有 1300 多家半导体相关产业,但其实不需要这么多,如果能减少一半可能情况会更好,而不是自相残杀,造成人才浪费,但因为厂商竞争太激烈,抢人不择手段,导致人才没有能扎实培养好技术的环境,另外是若能通过并购整合好资源,这也是非常重要。
虽然很多企业口号是自主、可控、安全,但实际上原创成分不高,有的说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也是一个口号,这个方向比较好,不是什么东西都要有原创,就怕没有原创反而造假就比较遗憾了。
并购这件事现在确实是存在问题,芯原做过几个并购,早期曾收购一家做 DSP 的,10 多年了主要人几乎都在,确保人才还是要看实际上的做法,去年也并购了一个 GPU 的团队。
收购虽然是取得人才与技术的捷径,但文化的整合很重要,即使能够买来,如果自己没有能力维持的话肯定也是不行的。
另外一方面,技术和人才的缺乏不能完全靠买就能解决,主要还是要靠自己培养,像紫光展锐就自己练了很多内功,真的是从毕业生开始培养,不仅人才有向心力,也能维持技术的一致性与可靠性。
戴伟民也提到,最近有一批从美国回来的人才,这些人的技术能力不差,如果把这批人用上去能够带新人的的话应该是不错。虽然这批人往往是技术很好,但就像大厨回来开餐馆,本来是烧菜的一把好手,开餐馆反而就弄砸了。
所以,为什么要投资这些人?就是为了引导他们。其实有很多人才浪费的地方,不一定是说人不够,重点还是去怎么利用好这些人。
群联电子董事长潘健成也提出自己的见解。
在闪存的系统里主控是很重要的,但主控赚不到钱就形成一个很大的矛盾,所以最大的主控使用公司全球有 6 家,他们大部分主控会倾向于自己来开发。比方说一个独立型的公司生存的空间是相对有限的,你要从你的商业模式转换出怎么让你可以持续地发展。

群联电子董事长潘健成
用这样一个思维来看企业要走自主开发、还是并购的路线,其实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对或错,如果今天一个新成立的公司,有钱、没有资源、没有人,那么就靠并购,先把第一步先迈出去,但群联电子 18 年以来是从无到有走过来的,到目前为止没有并购过一家公司,群联一年 10 个亿美金的营收是靠自己开发的产品慢慢把它积累出来的。
群联也发现其实在存储的领域里,靠并购效果会比较低,因为存储基本上要的是人,不是设备,做主控不是设备,是人。如果把人并购进来了,他不认同现有公司的文化,不认同技术方向,那并购过来的也只是一个空壳子。
当年群联到合肥去的时候,在当地确实请不到工程师,因为合肥本来就没有这个产业,后来想办法从上海、深圳找人回去,合肥毕竟还是第二线城市,不得已之下群联还是想办法自己来培养,经过 3 年努力,培养了 2 年之后,这些原本不懂芯片设计的人已经有能力可以自主开发产品给美国、日本的公司使用,这就证明一件事,事在人为,只要肯做,有魄力、有资源去做,并购不见得有必要性。
潘健成也认为国内其实不缺人才,但是缺专才。
如今从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其实就是人才,到产业去培养了专业能力,就成为了专才。这就好比小朋友考试,如果你给了 50 分的标准,那可能今天晚上用功复习明天就考 50 分了;如果你要他考 70、80 分,那在一个礼拜前用功复习,大概就能考 70、80 分了。但如果目标是要考 100 分,就不是临时用功复习就可以了,你必须每一天要把每一个基础做好,要很长时间去积累你的知识,重点是还不能犯错。
所以,在所谓的半导体 IC 设计里,必须要有一个很坚强的团队,这个团队要有默契地、很长时候地配合,然后一步一步地把 bug 理干净,这是需要时间的。
考试考 100 分不能靠运气,也不是短时间就能达到的目标,考试考 100 分是必须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累积出来,现在存储器人才挖角的这个气氛是必然的,因为毕竟国内政策鼓励存储器必须要能够自己设计、自己开发、自己发展、自己制造。
另外,潘健成也提到只想赚快钱所带来的问题。打个比方,有个人才今天刚毕业,到第一家公司先熬两年,本来 0 分的,现在能做到 60 分,觉得不错了,隔壁公司提出 2 倍待遇,然后就跳了,70 分的时候,另一家再说 2 倍,这次做到 75 分、到 80 分的时候,后来他变主管了,而当主管只有 80 分的时候,你期待在他带领下的团队能达到多少分?
根本的问题就是不能太浮躁,必须要有时间一步一步地把根基打起来,但另一方面,大家都要强出头也会成为问题,据说国内至少 100 家公司要做类似这种存储器主控产业,但这个市场并没有这么多空间可以分。意思是说 100 家这种公司中的大部分在未来两三年内一定会慢慢地被瓦解,最后兼并成少数几家存活下来,这个过程中的人力资源其实是浪费掉了,导致成本成长快,产品的瑕疵也会屡见不鲜。
所以,中国目前在产业发展上的浮躁气氛要稍微能够有所控制,人才能够在这个地方好好练兵、好像练功,把功力练好,对产业才有帮助,即便有政策支持,但如果经营者的心态还是想赚快钱,那么对整个半导体产业而言,依然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潘健成认为,以他在存储芯片的经验,要做好半导体产业就必须关注几个方向。
第一,要长期投资,玩短线的不会太好过,因为这个产业没有快钱,如果是做 U 盘、做记忆卡的主控,可以很快,一两年做一做,卖一卖,但毕竟这不是市场趋势,市场趋势是SSD,是NVME。
第二,不只长期投资,投资金额也要够高,半导体产业需要大笔资金来维持与研发。
第三,必须要有很强的研发团队,板凳要坐十年冷,“坦白讲在国内有多少工程师到少林寺把武功练完,打完十八铜人才出山的,比较少,通常是练了些粗浅皮毛就准备出山了。”所以对产品的成熟度,团队的长期默契,这是一个很大的隐忧。
由于群联在产品上要求是 100% 不得有瑕疵,所以团队比较要有很多年的积累、很多年的默契、很多年的团队合作,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应用材料集团副总裁、全球半导体业务服务群跨区域总经理余定陆表示,目前台面上的芯片设计公司都有这个问题,中国每年毕业生大概 900 万,这些人才如果要投入产业的话,做设备应该是这些人才的最后一个选项。

用材料集团副总裁、全球半导体业务服务群跨区域总经理余定陆
但大家以为做设备是一个机械设备,是跟机械有关,其实不是的。
其实应用材料在设备产业已经做 50 年了,设备的源头是深厚的科学基础,要怎样让所有的原子按预先设计好的方式跑到今天硅片上该有的地方,有时候还要让它停在那边,有时候还要去修改它,有时候还要教它走,这是一个科学,当你有科学的时候,设备只是帮你做到那个结果的工具。
但如果一个产业里头没有这样的人愿意进去把这些基本的东西做出来,那么要达到进一步的发展,不管是去制造、还是设计,要变成世界上重要的角色,其实非常困难、也是非常有挑战的一件事。
如果国内能够先理清这样的观念,然后国家在政策上去支持,愿意去投注这些产业的人才,这个才是比较有机会的。但这并不是在 2 年、3 年就能看到结果的东西,而会是一个 10 年、20 年、30 年的长期战略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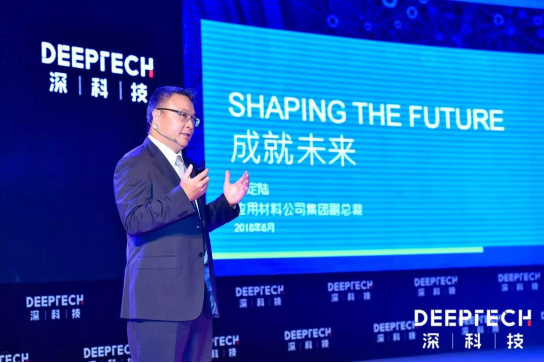
从应用材料的角度来看中国,有几个观点:
第一个,在中国,必须要去想想看发展半导体产业里面的生态链的策略,这变得非常地关键。所谓生态链的策略不见得是一定要当地化,而是说除了有一些自主能力,还要怎么样跟国际的伙伴互相连接。大家在生态链、生态圈里面共享利润、共享成功。这个策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二个,在中国,不管在半导体或其他产业,从 0 到 1 再到唯一,可以说是一个目标。当一家企业从 0 到唯一的时候,其实在生态里面就会变得不可取代,让企业的策略价值意义会变得提高,这对利润、后续的发展做到最大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第三个,关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在中国来讲是大家都知道的产业发展关键。因为有人口红利,所以推动各种产业的快速发展。
那如何在人口红利里面能够同时也发展出所谓人才红利?让这些人才产生有加成的作用,能够从一个人才到十个,到一百个,那么相关产业就可以持续壮大。
而对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来讲,余定陆总结:人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紫光集团全球执行副总裁兼紫光展锐CEO曾学忠认为,人才的来源要全球化,不只要从全球找人,更要从本土培养全球化的人,毕竟未来做生意不是只有在限定地区,而是要布局全球,如果只有本地人才,只懂本地的做生意方式,那要跨到全球就会很困难。

紫光集团全球执行副总裁兼紫光展锐 CEO 曾学忠
若从更高的层次来看人才问题,以紫光展锐而言,不仅是有中国的人才红利,全球的人才红利更应该重视。人才是任何一个 CEO 最关注的一个题目,曾学忠提出 3 个方向。
第一,全球化。在紫光展讯、锐迪科的核心人才里有四类人是全球化的人。
第一类:美籍的技术人才;
第二类:大中华区的人,类似像前者这样大中华区的人紫光展锐有一批,比如来自台湾、来自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顶级技术人才;
第三类:归国回来的中国人,在展锐一般是 VP、SVP 这一级;
第四类:自主培养的中国人。
这四类人才都是紫光展锐非常宝贵的全球化人才。
第二,自己培养+外部引进。
一个企业要成为世界顶级的企业,自己培养的人才一定是一个先导,就像自主创新是外部合作的先导一样。所以,从 2001 年展锐创办到现在还在工作的这些人才,他们慢慢地成为了顶梁柱。
当然,外部不管是通过并购、还是引进,对未来的方向、对创新的技术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第三,产学研合作。
中国或全球有这么多的高校,要把这些高校的智慧发挥出来,就成为产学研合作的重要成分。紫光展锐跟清华大学、上海的交通大学等都有非常好的产学研实验室,这些实验室既使这些老师、学生们学习,尤其很多学生能够到企业内部实习,有深度地合作,也能创作很多新的技术方向、新的思考。
曾学忠以其个人经验为例,刚到半导体行业的这半年也是很苦的,但能够跟这些全球最优秀的人才一起去工作、一起去奋斗,一起去实现梦想,并逐步实现梦想,其实还是很快乐的一件事。
